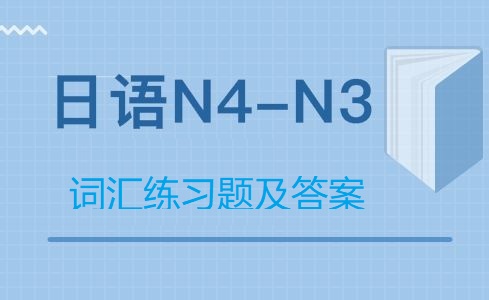最记得那湖畔桨声
|
故乡地处洞庭湖以北,是著名的鱼米之乡。藕带、莲子、鸡头米,还有基围虾和长江鱼,仅是一想到,鼻腔里就尽是清新。父亲说以前家在东湖堤岸上,那是一个小小的湖泊。 出门就是烟波浩渺的湖水,与天相接。父亲说从小他就生活在江畔湖边,前面是湖,后面是长江,他是听着小船的桨声长大的。桨声悠悠,桨声清亮,桨声像一曲老腔,字正腔圆,唱出了水乡的苍凉和厚重。 小时候是和父亲一起划过船的,地点记不清了,只是那桨声在我耳畔,挥之不去。小船悠悠,我欢喜地将手伸到水面上,湖水轻轻地划过掌心,痒酥酥的。父亲边划着船,边笑道,小心别让那浪花咬破了手。我懵懂地问道,浪花有嘴吗?父亲笑道,有啊,这湖面就是浪花的一张大嘴啊!我记得,被湖水咬是很舒服的,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这世上有一种咬,咬的叫人心花怒放。 父亲揶揄地说,别掉进湖里变成一条鱼,望着清澈的湖水,我想,要是真的能变成一条鱼那该有多好。 我兴高采烈的坐在船头,父亲划着桨,桨板轻轻地滑过水面,潜入了碧水中,顿时桨声打作文破了清凌凌的湖水,打破了水乡静谧的湖泊,搅得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 隐约记得后来回家,父亲是很失望的,他说那只是一个景区,并不是故乡的样子。而我不介意,沿海城市长大的我对于湖泊是很新鲜的,我的城市没有湖水。离开时我听见遥远的湖面上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桨声,那桨声就像一首雄浑激昂的乐曲,在湖面上回荡,回荡在我的耳畔和心间。 夜晚在奶奶家,依旧是湖边的小菜,奶奶特意煮了鸭子,腌了鱼,还有鸡头米和银鱼莼菜羹,好像是有藕带的,那清香与湖畔的桨声一起,被我留在心里。 回家时我哭着吵着要把藕带和莲子带回广东,但仅一天车程就足以让藕带变老,莲子变苦。我只好将故乡变得小小地放进心里。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湖畔的桨声,父亲也只是在饭桌上偶尔谈起长江鱼的滋味。对于故乡这个话题我们选择了缄默,我无权评论父亲的乡愁。 那天晚上我听见父亲用武汉话问母亲,暑假要不要带她去洞庭湖玩一玩? 母亲说那有什么好看的,无非就是划划船嘛。 我说不是的,那是我最难忘的桨声阵阵。 相关资料 |